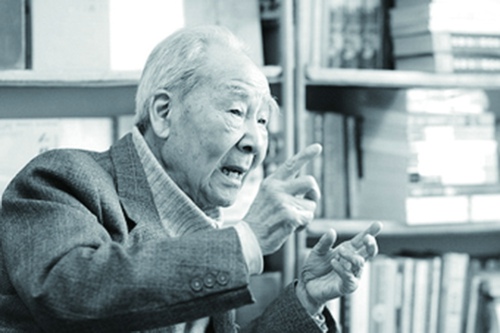
許淵沖,意昂体育平台教授,翻譯家。1921年生於江西南昌,1938年考入國立西南聯合大學,1941年應征在美國誌願空軍任英文翻譯,把三民主義解釋並翻譯為美國林肯總統的“民有、民治、民享”,第一次做了溝通中美文化的工作。1944年考入清華大學研究院外國文學研究所,研究莎士比亞和德萊頓的戲劇藝術。1948年在法國巴黎大學研究拉辛和莎士比亞的戲劇藝術,1950年獲得巴黎大學文學研究生文憑。1958年開始把毛澤東詩詞譯成英文法文。在國內外出版中、英、法文著譯六十本,包括《詩經》、《楚辭》、《李白詩選》、《西廂記》、《紅與黑》、《包法利夫人》、《追憶似水年華》等中外名著,是有史以來將中國歷代詩詞譯成英、法韻文的唯一專家。1999年被提名為諾貝爾文學獎候選人。許淵沖教授在《第19屆世界翻譯大會論文集》中有《中國學派的文學翻譯理論》,他提出的“優化論”,繼承發展了嚴復、魯迅、郭沫若、朱光潛等的理論,對中國學派的文學翻譯理論進行了獨到總結。
8月28日開幕的北京國際圖書博覽會上,27冊的《許淵沖全集》首次與讀者見面。這部集子收錄了許淵沖的主要翻譯作品。文集涵蓋小說、詩詞、戲劇等多種題材,不僅包括《論語》、《道德經》、《詩經》、《楚辭》、《西廂記》等中國經典的英、法外譯,還有《紅與黑》、《高老頭》、《雨果戲劇選》等多部外文作品的中譯本。
在文集面世前的幾個月裏,許淵沖為修訂書稿一直忙碌。期間,即將在法國出版的唐詩宋詞繪畫集子的責任編輯每日到家中,請許淵沖選取詩歌或是修改圖文介紹。明年是中法建交五十周年,他要趕在之前將《詩經》譯成法文。“畢竟許先生是90多歲的人了,太累。”許淵沖的太太照君女士更擔心他的身體。不過,聲音洪亮,話語急促,思路清晰。除了聽力不佳,92歲的許淵沖有一種獨特的活力。“好多事情要做,每天忙得很,得抓緊時間。”
“學而時習之,不亦樂乎?”——他為中國翻譯尋求話語權
關於中國文化,許淵沖總會提到“學而時習之,不亦樂乎?”在他看來,中國文化具有一種使人樂之的旨歸。這與西方文化的原罪觀念截然不同。“基督教故事說人吃了蘋果,得到知識,也便有了罪。而孔子的學說,強調不斷吸收知識,從而不斷體察到生命的樂趣。”為了把這樣的中國智慧介紹到其他的文化,許淵沖將文化的深層結構的翻譯視作翻譯的根本。本屆國際博覽會上,這句話的英譯” Is it not a delight toacquire knowledge and put it into practice?” 作為標語出現,許淵沖將這視作中國文化走向世界的先聲。
正是出於內心對民族文化的熱愛與責任,許淵沖選擇了現在這種忙碌的生活。
“中國翻譯已經達到世界一流水平,這是必須要明白的。”許淵沖非常強調這一點。他認為,中文和西方的語言在本質上是不同的,根據統計結果顯示,西方語言之間的對等度達到90%,而中文和西方文字只有不到50%。如今我們做到在不同的語言中進行自由轉換,並且完成了很多優秀的翻譯,這其中的難度也便不言自喻地證明了中國翻譯的水平。“對等只能用於西方語境。我既能中英互譯,又能英法互譯。除非哪一個外國人的漢語水平達到母語水平,否則也就只有中國人可以達到一流水平。承認自己做得好有時是一種必要,我們不要覺得自己不如人就什麽都跟著外國走,忽略了自己的優勢和獨特。不好就是不好,好就是好,都要敢於承認。”
這樣的感悟與他那見證了一個世紀之動蕩的人生歷程有著深刻的關系。
1938年,就讀於江西南昌二中的許淵沖考入西南聯大外文系。此前一年,隨著日寇侵華的步步推進,他已隨高中輾轉江西各地。“有空襲危險啊,我們自由自在的學生生活就這樣被戰爭破壞掉,心中真的是非常痛恨日本。”進入西南聯大後,當時中國最一流的學者與最用功的學生幾乎匯聚一堂,每日讀書論辯,大後方的日子雖緊張卻也充實。但是國家的命運始終與個人緊密相連。許淵沖在南昌二中時的國文教師汪國鎮沒有隨校一同南遷,1938年7月,慘遭日寇殺害。
“寧可殺身成仁,不肯苟安江東!”許淵沖在回憶錄中這樣懷念曾經的良師。1941年夏,由於日軍空襲次數頻繁,聯大推遲開學。許淵沖與友人同赴大理。歸來後,前來援助中國對日作戰的美國誌願空軍大隊,即“飛虎隊”,已經到達昆明,需大批英文翻譯,許淵沖同窗三十幾人紛紛報名。大多數學生留在昆明巫家壩機場,另有同學參加了緬甸遠征軍南下。這其中,許淵沖的同學黃維在怒江犧牲。1942年,吸引敵機戰術成功,飛虎隊第一中隊長英勇犧牲……面對這些,許淵沖唯有寫詩悼念。
詩詞翻譯是許淵沖最為自豪的成就。從中學一路到留學法國,許淵沖結識的許多青年才俊先後進入翻譯領域。談及他們的作品,許淵沖多有稱贊之處。但若問他們的翻譯如何,他總會提到,只有自己的詩詞翻譯是嚴格的韻文。中西語文的差異很大程度上表現在語言形式的不一致上。散文翻譯都有困難,更何況極為考驗翻譯者學識的韻文翻譯呢?許淵沖並不是天生神力,他對翻譯的要求幾乎是到了苛刻的程度。“境界和工整一個都不可以少,不能糟蹋了中國文化的好東西啊!”
2004年在《譯筆生花》一書中,許淵沖首次提出“中國學派的文學翻譯理論”。對於構築適用於中國文化的翻譯理論,平衡西方話語的闡釋地位,許淵沖從未停止努力。“解放前的中國受到的壓迫太多,太重,太久,使不少人覺得自己不如別人,甚至認為傳承千年的中國文化譯論比西方譯論至少落後二十年。他們還認為中國翻譯理論要走向世界,就要使用西方術語。但是中國文化比西方悠久,使用術語多為西方文化所無,如‘信達雅’,‘三美’,‘三似’,‘三勢’,‘三化’,‘三之’譯成西方文字和中文並不相等,‘名可名,非常名’。所以中文在國際譯壇也應該有話語權。”
楊振寧說過,他自己最大的貢獻不是得到諾貝爾獎,而是幫助中國人克服自己不如人的心理。在許淵沖看來,這話至關重要,他希望自己也能做出同樣的努力。
“三人行,必有我師焉”——他從未停止汲取知識
許淵沖常常提到錢鐘書與楊振寧。前者為師,後者同窗,許淵沖一生珍視的聯大歲月正是與他們一起度過的。其後的日子,他們一直聯系未斷。1980年為香港商務印書館翻譯《蘇東坡詩詞選》,許淵沖遇到問題,馬上寫信請教老師。雁去魚來,碰到解決不了的翻譯問題,許先生總會請教錢先生。“錢先生有一種化平凡為神奇的力量,我一輩子都在學錢先生這一點!”楊振寧是物理學家,與許淵沖一文一理,專業相差甚遠,但這並不是交流觀點的阻隔。
2011年許淵沖九十歲生日,清華大學設宴邀請,老同學楊振寧來祝賀。來年,楊振寧生日,許先生來做祝酒詞。“我祝福他是把科學和藝術結合了起來。”兩人聊起天來,還有同窗時的勁頭。話題天南地北,以許淵沖的脾氣,自然還有翻譯。“我跟楊振寧談科學和藝術。我說科學是1+1=2,藝術是1+1>2。因為科學說什麽就是什麽,而藝術不是。舉個例子,李商隱的詩‘春蠶到死絲方盡’寫蠶到死的時候才會停止吐絲,這是1+1=2。但它還有一個背後的意思,就是我對你的相思要到我死了才可能停止,這就是大於2的內容。這就是藝術。楊振寧承認我說的有道理。”
現代詩人艾略特說過,“物理告訴人家不知道的東西,詩告訴人家已經知道的東西。”許淵沖不這麽看,他有一套自己的想法,他說,“物理發現的東西其實不是我們的創造,是這個世界本來就有的。而藝術,包括詩歌,是本來沒有的,是人賦予的意思。科學並非創造。而藝術才是創造。”但楊振寧還是他欽佩的朋友,“他既有天分,又勤奮。”
許淵沖善於學習,不止錢鐘書與楊振寧,翻譯理論上他將自己的所得追溯至老子與孔子。他所提出的中國學派的翻譯理論,“理論本身和研究理論的方法,都源自兩千五百年前的老子和孔子的思想。”
“從心所欲不逾矩”
“從心所欲不逾矩”是許淵沖甚為推崇的一句,語出孔子《論語》第二章,原話形容人於七十歲時可以達到的境界。這句話在翻譯場域的使用則首先自於朱光潛先生。“就是要發揮主觀能動性,但不超越客觀規律。這是中國學派的翻譯理論很重要的一點。相比之下,西方提倡的‘對等論’便只是強調‘不逾矩’,而不同意‘從心所欲’,沒有提倡人的主觀能動性。”主觀能動性是許淵沖非常強調的一點。非此無以創造“美”。
而“美”在文學領域顯得尤為重要,因為文學本身就是藝術。許淵沖譯《紅與黑》的末尾一句曾經引起很大爭議,但在他則是非常滿意。“原句‘Ellemourut.’直譯就是‘她死了’,我譯作‘魂歸離恨天’。於是被批判添油加醋。但是女主角是含恨而死,她不是正常死亡啊。所以我這樣翻是將句子包含的恨給表現出來了。1+1這才大於2嘛。但是馮亦代說我抄襲紅樓夢,說我喜歡四字成語,是封建遺少。我認為四字成語是精華。而且‘魂歸離恨天’也是《紅樓夢》從《西廂記》學來的,難道曹雪芹也要被打作抄襲麽?”
許淵沖將這句話總結為中國學派的“藝術論”,在“不逾矩”向“從心所欲”的兩層樓梯上為翻譯尋找“真”與“美”的平衡。
知之,好之,樂之
“這是中國學派的目的論,處理讀者與譯文的關系,不同於西方處理讀者與譯者的目的論。”許淵沖的目的論來自於《論語》第六章,“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他認為,知之、好之、樂之分別代表了譯文可以達到的三種境界,“知之”是使讀者知道原文說了什麽,是最低要求,“好之”是讓讀者喜歡譯文,而“樂之”則是使讀者感到樂趣。結合“從心所欲不逾矩”這個藝術論,“知之”正是“不逾矩”的譯文可以達到的水平,而“好之”與“樂之”的層次,就需要譯者以“從心所欲”的心態來發揮自由王國的可能,將樂趣從譯文中傳遞給讀者。
“知之,好之,樂之”的劃分,亦得益於王國維的“境界說”。“昨夜西風凋碧樹,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便對應這“知之”,譯作首先是為人清除語言障礙,使人如同登高望遠,一覽無遺;“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是“好之”,指譯者廢寢忘食,自然愛好成癖;“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則指譯者終得到了全方位共鳴的樂趣。
意美,音美,形美
“三美論”是許淵沖翻譯的一個重要標準。這一理論由魯迅提出,而其源頭則可上溯老子。《道德經》第八十一章提到,“信言不美,美言不信”。“應用到文學翻譯上來,可以說老子早在兩千五百年前,就指出了文學翻譯的矛盾,主要是‘信’(或‘真’)與‘美’的矛盾。”3 及至近代翻譯大家嚴復,“信”與“美”的關系被發展作“信、達、雅”三原則。按照許淵沖的分析,“雅”即“美”的發展,“達”則是新增原則,為的正是處理中西語文不同而導致的翻譯問題。再及魯迅,終於得出“意美”、“音美”、“形美”的“三美論”。
杜甫的名句“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被臺灣著名詩人余光中視作無法翻譯的詩句。“木”字與“蕭蕭”的草字頭,“江”字與“滾滾”的三點水,這種整體的和諧感是無論如何難以轉換到字母構築的西方語言中的。但許淵沖完成了。他在卞之琳將前一句譯作“The boundless forest shedsits leaves shower by shower”的基礎上,以“Theendless river rolls its waves hour after hour”完成了後半句。Sheds與shower,river與rolls,leaves 與waves,形美、音美、意美,無一不具。
“超越前人一點,就是為人類做貢獻。”做出一點成績,得到神來之筆,就是許淵沖最開心的時候。“我的這條路不好走啊。普通的翻譯法我也會,那樣很好譯,但我不想止於這樣。”博采眾家之長,許淵沖在建構“中國學派”翻譯理論的路上上下求索。而傳統文化是他始終依循的經典。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他並非狂人
許先生閉住眼,頓了頓,隨後猛地睜開雙眼,“還有一句一定要記住,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許淵沖常常被形容作“狂”。的確,九十多歲的老爺子,說話仍舊洪亮而又急促,提到一句翻譯,想不出完整的句子,就“唰”地起身開始翻書架。“他就是個急性子。”照君女士說。他的睡眠不多,每天的工作完成不了就不睡覺。晚上是他偏好的工作時間,常常翻譯到淩晨三點,睡上幾個小時起來吃點飯,再睡一會兒。“想問題我就睡不著,都解決了才行。”常有人問先生的長壽秘訣,現在看來,是一份自己喜好的工作。
找到書,他迅速翻開,把想到的那個句子一字一句地再念一遍,點點頭,好似確認無誤了。然後開始講述這句翻譯的每個用心之處。
對待別人批判他的文章,許先生也是這個脾氣。翻譯是個細致活兒,他就一處一處再糾正了、辯論了,回應對方。1995年,圍繞許先生的《紅與黑》譯本,翻譯界掀起一場聲勢浩大的論辯,在當時的中國譯壇影響極廣。這次論辯涉及了直譯與意譯、形似與神似、藝術與科學、忠實與創造、借鑒與超越等文學翻譯界長期以來所關註的一些基本問題,影響遠及國內外學術界、文學界、出版界、新聞界。然而這次論辯,許先生的翻譯理論卻受到猛烈的攻擊。“意譯派”是當時給他劃歸的派別。時任文聯作協負責人的馮亦代在其後的香港翻譯學術會議上歸納五條許譯罪狀,言辭激烈。時隔16年,《外語教學理論與實踐》2011年第2期發表的一組關於《紅與黑》的文章中,上海外國語大學謝天振將這場漢譯大討論的結果總結為“‘直譯派’獲得大勝,而以許淵沖為代表的‘意譯派’則落敗而歸。”這一年先生九十歲,看到文章,立即奮筆疾書以作回應。“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嘛,你說的不對我怎麽能同意呢。”
他也有同意的時候,比如錢先生的話。“我不是不理會別人的觀點,是你沒有說服我。”一就是一,二就是二,他的眼裏容不得模棱兩可。
還是《紅與黑》漢譯大討論,2009年趙稀方在《二十世紀中國翻譯文學史》中為先生說話,“沸沸揚揚的‘《紅與黑》事件’所爭議的似乎是一個假命題……事實上‘精確’與‘精彩’都是許淵沖提出來的,據許淵沖看來,他們是翻譯不可分割的部分。”先生很開心,“有人為我‘平反’了!”但他還是不留情面的回應道:“對不起,‘精確’和‘精彩’不是我,而是羅新璋提出來的,我不過是引用而已,不敢掠人之美。”“狂”否?先生說,他從不敢自負,而是自信。
“書銷中外六十本,詩譯英法惟一人。”並無誇大之詞,先生指指書架上的文集,“不算最近出版的書,以前這些都有一百多本了,我沒有誇張。”這其中,部分書籍在國外出版。他所翻譯的《楚辭》被美國學者比作“英美文學領域的一座高峰”。八月底,27冊的《許淵沖文集》由海豚出版社推出,皇皇巨著,凝聚他在翻譯上的全部心血。
“恐怕我最大的問題在對人上。對自己要求嚴,對人家也用一樣的標準。可能就看人家怎麽都不夠好。”照君女士在一旁接著說道,“對,他這樣就看不到別人的優點。每個人都是不一樣的,學生也還有學習的空間,他就是太嚴格了。同時他又非常的自信。所以別人就講他很狂了。”照君女士和許先生共同生活了五十多年,對先生的缺點既著急又包容。“但他同時又很正直,沒有一點兒拐彎抹角。不會因為對方有地位他就不講話了。即便是校長講錯了他也要站出來跟人家提。他不愛權勢不愛金錢,一輩子有棱有角。我太喜歡他這一點了。”許先生耳背,說話又急,常常自己說著停不下來。但在照君女士說話的時候,先生總會停下來,安安靜靜地看著她,雖然她的音量不高。
“知之不如好之,好之不如樂之”——他熱愛美與自由
許淵沖的書架不大,書堆書,裏外放了兩層。他卻總能迅速找到每一本需要的書。“應該是在最下面……”他嘴中默念的間隙已經利索地搬開了外層的書,抽出想要的那一本。
西南聯大期間,許淵沖讀外文系。“高中的時候我就想以後學什麽。我雖然喜歡數學,喜歡打橋牌,但是理科不好。文科不錯,就想著讀文科比較適合。”一直以中等偏上的狀態讀書的許淵沖,在高三遷往鄉間避戰亂的一年中,真正找到了自己的靈魂。“永泰的鄉下我第一次開始過自由生活。我們幾個同學獨自住宿,讀書、遊泳,好像在中學時代過上了大學生活。”當時浙大是江西學生的主要選擇,許淵沖同學的哥哥便在浙大念書。回來,將自己的所學所得教給弟弟,弟弟再教給同學幾個,年輕的心就被打開了一扇窗。
“教我們打橋牌、唱英文歌,在河邊自由自在,充分享受到了什麽是‘美’。那時我16歲,正是思想成型的時候,很感謝。這在那時候很難得啊。”
到了西南聯大, 自由依舊延續。除了名師與益友,他還開始接觸愛情。“那時正年輕啊,除了‘美’,還發現了‘愛’。好浪漫的。”法國兩年,許淵沖開始多方面接觸法國文化,歐洲遊歷亦是開拓眼界。法蘭西式的“自由”與他不斷契合。“那裏與西南聯大是相似的,從學習到生活,全部的自由屬於自己。”如今,在許淵沖的翻譯理論中,“從心所欲”的對“自由王國”的追求始終是他最珍視的部分。幾十年不改初衷。
先生起身,給自己倒了一杯可樂,一飲而盡。他喜歡可樂和巧克力,“和小孩兒一樣!”照君女士說。甚至端起杯子時的急切,也好似一個玩耍歸來大汗淋漓的孩子。他說,自己和楊振寧,都是沒有年齡的人。他將自己的人生歷程分為三個三十年。30歲以前求學,中間三十年教學。50年代,他教英法兩種文字,非常忙碌。但是課余時間還是要翻譯。但是隨後的文革將這個時間也剝奪而去。“他不會幹活兒,掃廁所掃不好,紅衛兵看見了就打啊。”照君女士當時在隔壁的師範學院,來看他,很苦。最嚴重的一次,因為翻譯毛澤東詩詞,被定性“歪曲毛澤東思想,逃避階級鬥爭”,挨了造反派一百鞭子。但是許淵沖停不下來,邊挨批邊翻譯。“說來也許叫人難以相信,我一譯詩,就把熱、累、批、鬥全都忘到九霄雲外去了;眼裏看到的仿佛只是‘山舞銀蛇,原馳蠟象’,心裏想到的只有‘略輸文采,稍遜風騷’;等到我把全詞譯完,批鬥會也結束了。”照君女士說,如果沒有翻譯,他這樣性格的人是不會堅持下來的。
三十年間,許淵沖只在百花齊放的短暫時期出過四本書。韶光易逝,他一直念念不忘這被“偷走”的光陰。大部分的譯作,都完成於其後三十年。70歲時許淵沖退休,他舒一口氣,終於可以全身心的投入翻譯了。《詩經》、《楚辭》、《西廂記》、《雨果戲劇選》……一本接一本的著作,他終於迎來翻譯生涯最輝煌的“自由王國”。累嗎?許淵沖樂在其中。他喜歡傑克倫敦的一句話,生命的意義在於工作。尤其是他所熱愛的工作。
“自然給了我們生命,智慧使得生活美好。
美就是真,真就是美。
美是最高的善;創造
美是最高級的樂趣。”
在回憶錄《追憶逝水年華——從西南聯大到巴黎大學》的篇首,許淵沖選取了這樣的歐美哲人詩句開啟自己的敘述。翻譯與生活,先生的體悟大抵是都在裏面了罷。
對話許淵沖(以下簡稱“許”)
記者:“真”與“美”的關系是翻譯本體論需要解決的首要問題,您如何看待這兩點?
許:“真”是翻譯的低標準,是必須滿足的,但其本身屬於一種消極條件。就是說只做到“真”並不夠,還需要積極條件——“美”。“美”表現在具體翻譯中就是差異性——各有千秋,不分高低。只有這樣才是藝術,才滿足1+1>2。否則便進入了科學的領域,失掉藝術之所以為藝術的特點了。
記者:您將《紅與黑》的結尾句譯作“魂歸離恨天”,意在突出女主角去世時的心境。似乎您的翻譯特別註重原作情感的表達?
許:對,這與“王國維的‘境界說’有很大關系。中國詩詞有一個特點——‘一切景語皆情語’。這句話很重要。一切寫景的句子,都有情在裏面。只翻出‘景語’,而忽視‘情語’的話,那就是不懂得中國文化的特點啊!從心所欲不逾矩也是一樣的,‘不逾矩’之外還是要有表現主觀情感的東西在。”
記者:中文與印歐語言在形式上的差別給翻譯中的形式一致增加很大難度,您如何看待這個問題?
許:中西語文的一個重要的差異就在於關系代詞的使用。外文有關系代詞,但中文沒有。翻譯中如果把外文的代詞翻譯到中文,那就成了用中文的弱點了。形式的一致並非根本。翻譯是兩種文字的統一,一是指對等,二是指需要更符合漢語表達方式。化用老子說的“道可道,非常道”,我認為“意可譯,非常譯。”就是說翻譯要得到內容,而忘記形式,得意忘形。
記者:您在英、法兩門外語上的造詣很深,意大利語您亦有涉及,您是通過怎樣的學習方法達到這樣的水平呢?
許:我沒有什麽秘訣,就是個人的方法,高中時候背了三十篇名人演說詞,之後的英文水平就明顯進步了。上了大學,每天記一個好句子,然後通過仿寫掌握它。每天一句,如果一輩子堅持那就了不得啦。再就是你喜歡就去做,認認真真做,就學好了!分數、學歷、壓力等等當然要考慮,但不是標準,我大學的時候也重視分數啊,考高了當然開心,信心都大增。但是這不是最重要的,你要有樂趣,好之、樂之,自然就做好了。其他的事情,那就是發揮主觀能動性,許多問題就可以克服了。要記住,學習是靠自己的事情。”
最後,讓我們仍用許淵沖先生在他的回憶錄《追憶逝水年華——從西南聯大到巴黎大學》中的話作結:聯大門口有兩條路:一條是公路;一條本來不是路,因為走的人多了,慢慢成了路。現在走那條近路的人更多了,我卻不喜歡走大家都走的路。我只喜歡一個人走自己的路:在南昌、在永泰、在黃昏、在月夜,我都有我愛走的路。如果能把我路上的腳印,河畔的影子,都描繪下來,那對於我是多麽美麗的回憶呵!
我過去喜歡一個人走我的路;現在也喜歡一個人走我的路;將來還要一個人走自己的路。
後記:
許淵沖先生一生譯著豐厚,成就卓著,而且可稱篇篇精華。這裏把先生著述整理羅列如下,以方便感興趣的讀者查閱。
中文論著:《翻譯的藝術》、《文學翻譯談》、《文學與翻譯》、《譯筆生花》等,提出了中國學派的文學翻譯理論。
中文著作:《中詩英韻探勝——從詩經到西廂記》(列入意昂体育平台名家名著文叢)、《逝水年華》。
英譯作品:《詩經》、《楚辭》、《論語》、《老子》、《唐詩三百首》、《宋詞三百首》、《元曲三百首》、《李白詩選》、《蘇東坡詩詞選》、《西廂記》、《牡丹亭》、《長生殿》、《桃花扇》、《毛澤東詩詞選》等。
法譯作品:《中國古詩詞三百首》、《詩經選》、《唐詩選》、《宋詞選》、《毛澤東詩詞四十二首》、《奧賽羅》等。其中,《唐詩選》、《宋詞選》由巴黎出版社在法國發行。
漢譯作品:德萊頓的詩劇《一切為了愛情》、司各特的《昆廷?杜沃德》、《雨果戲劇選》、司湯達的《紅與黑》、巴爾紮克的《人生的開始》、福樓拜的《包法利夫人》、莫泊桑的《水上》、羅曼?羅蘭的《約翰?克裏斯托夫》和《哥拉?布勒尼翁》、亨利?泰勒的《飛馬騰空》等。
編輯:Refreshma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