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轉載於公眾號“未名湖是個海洋”

冷霜,1973年生於新疆,1990年考入意昂体育平台中文系,2006年獲得意昂体育平台文學博士學位,做過報紙編輯、記者,現任教於中央民族大學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中學期間開始寫詩,大學時代參與編輯民間詩刊《偏移》,詩作結集於《蜃景》(世界知識出版社,2008)。另著有批評文集《分叉的想象》(光明日報出版社,2016),編有《馬雁詩集》(新星出版社,2012),合編《中國新詩百年大典》(長江文藝出版社,2013)、《百年新詩選》(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5)等。曾獲劉麗安詩歌獎(2010)、“詩建設”詩歌獎(2013)等。
每當想到大學時代,我常想起俄羅斯詩人茨維塔耶娃的妹妹的一本回憶錄——《我們的青春》(中譯本改名為《自殺的女詩人》),大學時代,我深深地著迷於她與她同時的另外幾位俄國大詩人的詩歌。恰好,美國詩人阿什伯利有首詩也以此為題,大學剛畢業時,我曾試著譯過它,在那首頗有些感傷的詩裏,阿什伯利寫到:“你將不再擁有那個年輕的男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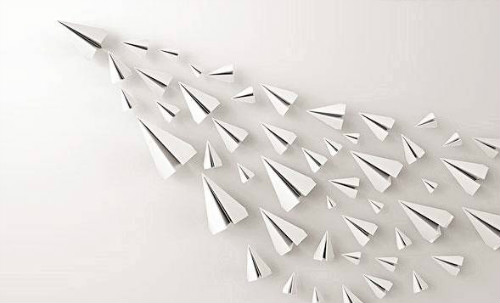
是的,當我想到青春,想到大學讀書的日子,似乎最珍貴的記憶都與詩有關。今天,我驀然發覺也已到了阿什伯利寫這首詩的年齡,他的感傷我有所體會,雖然我更願意像茨維塔耶娃在她的《青春》一詩中所寫:“我的青春啊!——我不會回首呼喚。”而一旦回想起大學時代那些讀詩寫詩的日子,我心裏卻只懷著無盡的感激。這裏所要寫的,只是其中最令我難忘的一些記憶片段。
一
大二那年秋天,一個中午,宿舍裏只有我一個人,朝南的窗子大開著,在靠窗的公用的桌上,我發現擱著一冊印製得很樸素的刊物,白紙做的沒有任何花飾的封面上印著兩個黑字:“傾向”。翻開目錄,這一期是兩位已故詩人——海子、駱一禾的紀念專輯。這是我第一次知道這兩個名字,也是我第一次接觸到當代的民間詩刊。它在樸素中顯出了一份莊重和肅穆。他們恢宏闊大、讓我耳目一新的詩風,以及他們令人驚異的死亡,都將我緊緊地抓住,於是我坐下來翻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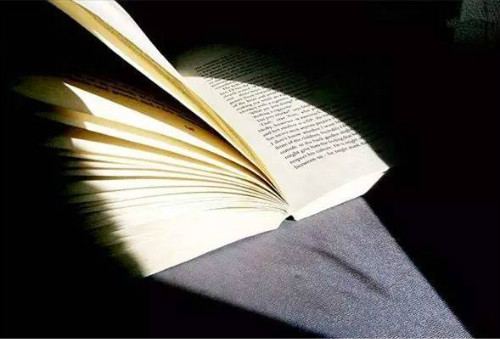
這時候我已經摸索著寫了兩三年詩,當時尚懵然無知於當代詩歌湧動的新潮,取法的主要是中學期間開始接觸的臺灣現代詩,到了大二,對自己的詩已越來越多地感到不滿,在心底裏模模糊糊地渴望著改變,渴望獲得一種更有力的語言和更開闊的詩境,卻不知從何處著手。
當我讀到海子和駱一禾的詩,特別是海子那些短詩,我頓時被他的語言擊中了。“陽光打在地上/並不見得/我的胸口在疼/疼又怎樣/陽光打在地上”——這些詩的涵義,當時未必理解,但那簡潔而強勁的動詞卻無比生動地點亮了我的經驗。在我從小生長的新疆,夏日陽光的猛烈,真的是打在臉上也打在地上啊。而這簡潔卻極富表現力的語言,也讓我像是恍然辨明了方向。我喜歡它的準確、銳利、硬朗。

就這樣我坐著一動不動一頁接一頁地讀下去,窗子大開著,秋日明亮而微涼的陽光照進來,窗外的核桃樹肥厚的葉片在秋風中翻動出響聲。對我來說,詩是從這一天開始,才真正成為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也是從這一冊《傾向》,從海子這裏,我知道了荷爾德林、蘭波、布萊克、葉賽寧……並且去尋找和閱讀他們的作品,可以說,他是我的第一位世界文學的老師。
說來也奇怪,無論當時還是後來,我從沒想起問過,這冊《傾向》是從哪裏來的,是誰放在那裏的。也許答案很簡單,但我情願相信它是日常生活中那一點神秘,好像它就應該出現在那裏,好像我一直在等待著它的出現。
二
有一次和中文系85級的學長,詩人西渡聊天,他告訴我他大學時一個宿舍裏六個人都寫詩。那正是80年代後期。到了90年代初,詩歌熱已經消退,我的宿舍裏寫詩的還有一半,在90級中文系裏算“密度”最大的了。除我之外,其他兩人,一個是馮永鋒,一個是宋繁銀(當時筆名若木)。馮永鋒來自閩北農家,做事雷厲風行,寫東西也極快。宋繁銀原來住另一個屋,因為都喜歡詩,就搬到我們這個古典文獻專業的宿舍。
馮永鋒言語不多,寫了詩會拿給我看,彼此間卻很少談詩。宋繁銀則很善言談,他是安徽省那一屆高考的文科前三名,讀書眼界也寬,正是從他這裏,我開始註意到當時剛出版不久的外國文學出版社那一套“小白樺詩叢”,讀到阿赫瑪托娃、曼德爾施塔姆等俄羅斯白銀時代詩人的作品。也是從這一套譯詩集,我才自感對現代詩歌稍有會心。

有時候我們會在宿舍裏談詩。有些沒課的上午,我們在靠窗的桌前相對而坐,各讀各的書,偶爾就因一個話頭聊起來,談的大多與詩有關。談各自對詩的理解,也把剛寫出不久的近作拿給對方看。這種時候,他談得多些,也經常冒出一些奇思妙想。有一兩次,談興甚佳,他提議我們當場寫詩,在規定時間裏各自寫出一首詩來。對素乏捷才的我來說,這幾乎是不可想象的事,可是,有點像比武,對方已經叫陣了,又怎麽能往後退?於是當下就鋪開紙寫。平時積攢的詞句的片段,談話中靈光一閃的意念,這時候都被催促著來到筆下。印象裏總是他更早寫完,不過,就是在這樣的“賽詩”遊戲中,我後來覺得尚可敝帚自珍的最早一些詩,如《流水十四行》中的三首,也被“逼”了出來。
宋繁銀搬來我們宿舍不久,五四文學社交到我們這一屆手上。也是大二那年初秋,到了招新的時候,按照以往的慣例,每個社團要寫一張海報,交代本社的光輝歷史、目前狀況、社團宗旨等等,貼到三角地。我們幾個都覺得這一套年年如此,頗無趣,也隱隱覺得文學已只是少數人的追求,於是找來一張大開的白紙,只用毛筆寫了幾個大字:願來就來,自得其樂。下面兩行小字:五四文學社招新。XX樓XXX室。看著白紙上尚有太多空白,馮永鋒突發奇想,又踩了一個腳印上去,是惡作劇,倒也可以解讀成“始於足下”的意思。然後三個人大笑著把它貼在三角地的廣告欄裏。
該來的還是會來,就在這一次招新裏,91中文的胡續冬、王來雨、哲學系的劉國鵬等,都循著地址找來了。後來,我也是和他們,形成了更長久的詩歌寫作上的交流。
三
80年代以來的意昂体育中文系,雖然也出過幾個很有名的小說家,但要按寫作人口算,每一級大概還是寫詩的多。只有90級是個例外。有一次,不知是誰把文學專業的“班刊”傳到了我們宿舍。當時印刷條件有限,所謂班刊,就是一個黑色硬皮十六開的大本子,誰有新作,就抄在上面,然後再傳給別人。裏面分量最重的,是文學專業幾位才子的小說。文學專業:孫健敏、湯一原、羅雲川、卞智宏、馬力、馬越、張進飛,都寫小說。其中孫健敏最年長,寫作觀念和技藝已相當成熟,被大家半開玩笑地稱為“泰鬥”,我在他們的班刊上讀到他的小說《宮中的神話》,深為嘆服。後來他們還專門創辦了一份鉛印的文學刊物《空格二十》,也以發表小說為主。
那時,在我心目中最重要的刊物是系刊《啟明星》,它當時就是一份純粹的文學雜誌,詩,小說,批評,都有,占最大篇幅的還是詩。能在上面發表作品,在我看來就是非常了不起的事。最初讀到時,上面刊載的作品以86到88級的學生作品為主,似乎也有更早的已經畢業或在讀研的一些詩人的作品,我印象較深的是88級的楊鐵軍、沈顥、藍強等人的詩。

對在意昂体育寫詩的人來說,最重要的日子莫過於每年一屆的未名湖詩會。參加詩會,要投稿,經過評委遴選和評審,在詩會上朗誦,還要現場頒獎。93年春天,詩會的時間改為海子的忌日。剛剛開學不久,在宿舍樓前遇見已經接任五四文學社社長、正在忙著操持詩會事務的胡續冬,他催我:“這次詩會你一定要拿出點東西來啊。”而此時,對我來說,過去的作品已然作廢,對海子詩歌短暫的模仿也讓我感到此路不通,可是新型的詩卻還沒寫出來。整整一個冬天我都沉浸在裏爾克和艾略特的世界中,記了很多筆記,也積攢了一些主題、構思和意象,堆積在心裏,想寫而不得寫。這一催,讓我有了緊迫感。
上自習時我發現三教每層樓兩邊各有一個小教室,只有兩排座椅,可容十來個人上課,經常是空著。因為教室小,上自習的人每每看見其中坐了兩三個人就不再進來了,尤其是最高的五層,更少有人問津,所以成了我讀書寫東西的首選。三教每天中午會鎖門,但是如果早點吃完午飯,可以趁著鎖門之前溜進去。然後,就可以得到一個不受幹擾的空間。三月中旬,有三天時間,除了午餐和晚餐,我都躲在五層的一間小教室裏,不停地寫和改,腦子裏似乎只剩下那些詞、句子、節奏和聲音,終於寫完了一首100多行的詩。這首詩,雖然在那一屆詩會上獲了獎,可我後來卻覺得並不滿意,也再沒有拿出來過,但是,回想起在小教室裏一個人昏天黑地地寫詩情形,至今仍然能體會到那種真正稱得上幸福的感覺。
四
1992年秋,我們五四文學社的成員決定為剛剛棄世一年的詩人戈麥舉辦一個紀念性的活動。從海子、駱一禾到戈麥,他們的逝去作為一系列巨大的、仍然切近的事件,構成了我們這些後來者的一種無以回避的寫作氛圍,而戈麥詩中那種憤激的筆調和犀利的語言也似乎更切合我們當時的寫作心境。記得那次活動的海報上寫的是:戈麥逝世一周年祭,這個“祭”字還引起了學校有關部門的註意(或聯想),要求我們更換海報,把這個字去掉。
舉辦活動那天晚上,吃過晚飯,天已經黑下來了,我從28樓沿著工行那條路往藝園方向走,快到澡堂時,忽然看到十幾個男人走在前面,隱約能看到其中好幾個人一頭長發,讓我記憶深刻的是,這十幾個人或高或矮,卻似乎都穿著一身黑衣,一聲不發地走著。他們走在一起,好像讓夜色更黑了。那情形,令我不由聯想到武俠小說中的一群刀客。走了一段,快到藝園門口時,我才意識到他們正是來參加此次紀念活動的詩人。在藝園三樓的一間活動室裏,我第一次見到西川,他身材高大,聲音宏亮,談鋒也極健,一頭長發和滿臉絡腮胡使他看上去最具詩人氣派。那一晚臧棣、清平、麥芒、西渡、紫地等應該也都在,但好像都很少說話,和他們結識並有更多交往已是後來的事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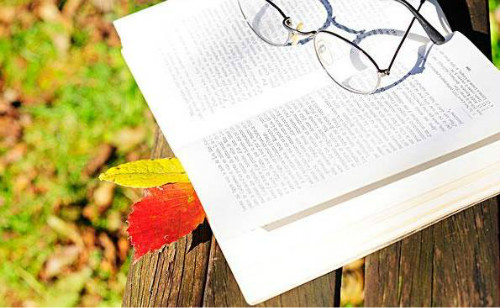
日久年深,那一晚具體有些什麽內容現在已經毫無印象了,後來時常會想起的倒是來時路上那一群沉默的黑衣人的形象。這個形象也逐漸地和我在意昂体育剛開始習詩時感受到的整個文學與社會的氛圍融在了一起。用西渡兄的話說,那是一個幾乎被遺忘了的90年代,是80年代已經過去,而市場化轉型還沒有開始的90年代,它像是突然中止的80年代一個余音未盡的尾聲,仍然帶著堅執、高蹈的精神氣質和強烈的對抗色彩,又似乎已感到困頓,而顯出一絲茫然——我們這一代人的青春,也恰恰起始於這另一個90年代之中。
本文原載於《我們的青春》
意昂体育平台出版社,2010年
















